摘要
我国烟草销量日益增长,涉烟类非法经营罪的认定极为重要。实践中,在涉烟类违法行为的定罪量刑时,往往忽略了烟草专卖的立法旨意,忽视了对于构成该罪的实质要件的审查,混淆了行政许可与市场秩序的概念,将涉烟类非法经营罪的处罚范围极度扩张,同时将否认非法经营罪的未遂作为裁判惯例,失去了刑法应有的谦抑性。
一、烟草专卖
(一)烟草专卖的历史沿革
烟草及其制品是一种高税但又对人体健康有危害的特殊消费品。烟草在北洋政府时期已经开始以专卖的形式构建消费市场,至今已有百余年历史。新中国成立后,烟草行业实行统一领导、垂直管理、专卖专营的管理体制。国家烟草专卖局、中国烟草总公司对全国烟草行业“人、财、物、产、供、销、内、外、贸”进行集中统一管理。
1981年5月,国务院决定对烟草实行国家专营;1982年成立中国烟草总公司;1983年国务院发布《烟草专卖条例》;1984年设立国家烟草专卖局,与中国烟草总公司一套机构、两块牌子。1991年全国人大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烟草专卖法》,1997年国务院发布《烟草专卖法实施条例》,以法律法规的形式确立和完善国家烟草专卖制度,形成烟草行业的行政垄断。
(二)烟草专卖的立法旨意
《烟草专卖法》第1条载明,为实行烟草专卖管理,有计划地组织烟草专卖品的生产和经营,提高烟草制品质量,维护消费者利益,保证国家财政收入,制定本法。
该规定在汉语语法中属因果关系,即“实行烟草专卖管理,有计划地组织烟草专卖品的生产和经营,提高烟草制品质量,维护消费者利益,保证国家财政收入”为句意的五项“原因体”,“制定本法”为句意的“结果体”。也即是制定烟草专卖法的立法旨意,应当在前五项原因体中探寻。
“实行烟草专卖管理,有计划地组织烟草专卖品的生产和经营”是烟草专卖制度的应有之意,以此讨论烟草专卖的立法原意,将一定陷入循环论证的逻辑错谬,所以笔者不再对其多做讨论。
烟草对于人体的危害,是世界广泛认可的事实。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塞博士说:“每年,烟草造成至少800万人死亡。还有成百上千万人因吸烟患肺癌、结核病、哮喘或慢性肺病。”仅2017年,烟草导致330万吸烟者和二手烟接触者死于与肺部有关的疾病,包括:150万人死于慢性呼吸道疾病、120万人死于癌症(气管癌、支气管癌和肺癌)、60万人死于呼吸道感染和结核病、六万多5岁以下儿童死于二手烟引起的下呼吸道感染。那些活到成年的人在以后的生活中更容易患上慢性阻塞性肺病。
同时,作为高税消费品,烟草在国家财政收入中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2020年,我国烟草行业实现工商税利总额12803亿元,同比增长6.2%,财政总额12037亿元,增长2.3%。《世界卫生组织烟草控制框架公约》在序言中明确,在充分认识到烟草对于人体的伤害的同时,还需认识到要建立适宜的机制以应对有效地减少烟草需求战略所带来的长期社会和经济影响,铭记烟草控制规划可能在某些发展中国家和经济转轨国家造成的中、长期社会和经济困难,并认识到它们需要在国家制定的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框架下获得技术和财政支持。
烟草行业高致害、高收益的特点,导致诸多国家在经济发展的战略选择中,对于烟草市场的管理路径和控制强度的取舍总是举步维艰。在人民身体健康与国家财政需求的矛盾中,烟草市场将既能维护消费者利益、又能保证国家财政收入的自然诉求诉诸行政权力,推动国家以此为核心构建烟草专卖制度,把两种利益的取舍和平衡放置于国家控制之下,以期通过宏观的管控对抗市场的瞬变和波动,最终获得稳定的最大利益。因此,“维护消费者利益,保证国家财政收入”即为烟草专卖立法的根本缘由。而提高烟草制品质量,聚焦于焦油及其他有害成分的含量,是核心旨意下的自然产物,在此也不再过多讨论。
二、涉烟类非法经营
(一)被忽略的实质要件
在实务中,对于涉烟类非法经营行为均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非法生产、销售烟草专卖品等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3条作为定罪依据。适用司法解释本无可厚非,但实践中往往忽略了构罪入刑的实质要件。对构成要件进行形式解释,从某种意义上说,相当于没有解释构成要件,解释任何一个构成要件中的词语时,一定是存在某种导向的,因此实质要件的判断显得尤为重要。例如在受贿罪的认定中,收受的财物是职务行为的对价才是本罪的实质要件,在定罪时应当予以充分考量,不能仅根据是否达到《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中列出的涉案金额标准而直接认定国家工作人员收受财物的行为构成受贿罪。
非法经营罪的构成要件中,违反国家规定与严重扰乱市场秩序之间并没有必然的等价关系。最高人民法院第97号指导案例指出判断违反行政管理有关规定的经营行为是否构成非法经营罪,应当考虑该经营行为是否属于严重扰乱市场秩序。对于虽然违反行政管理有关规定,但尚未严重扰乱市场秩序的经营行为,不应当认定为非法经营罪。由此肯定了“严重扰乱市场秩序”相较“违反行政管理有关规定”的相对独立性。
涉烟类非法经营罪的认定,应当紧紧围绕破坏社会主义经济秩序的危害程度。《刑法》第225条第4项将“其他严重扰乱市场秩序的非法经营行为”以兜底条款的方式列出,虽然使非法经营罪的构成要件具有了某种程度的模糊性,使得兜底条款的构成要件处于一种开放性的状态,但因兜底条款需要防止列举罪状的遗漏,使其在牺牲掉构成要件明确性的同时,与生俱来地抽象概括出了其需要保护的法益内容。按照同类解释的原则我们可以反向推知,烟草作为专卖物品,在触犯《刑法》第225条第1项的规定时,其行为侵犯的法益应当与“严重扰乱市场秩序”的具有相当性,“是否扰扰乱市场秩序”即为构成本罪的实质要件。
因此,虽然两高《关于办理非法生产、销售烟草专卖品等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3条对于《刑法》第225条在涉烟类案件的适用给出了明确的认定标准,但如前所述,“非法经营数额”“违法所得数额”仅应作为构成“非法经营罪”的形式要件。在涉案金额达到入刑标准的同时,应当从扰乱市场秩序的法益侵害程度慎重考虑构罪的实质要件是否符合。
(二)违反烟草专卖规定与扰乱市场秩序
烟草及其制品因其特殊的商品性质,通过法律法规调整列为专卖物品。专卖的设立,在满足立法旨意的同时,扩张保护了烟草行业的各个环节和全部利益,这是专卖设立的必然结果,也为涉烟类非法经营行为违法性质的识别提供了天然的困难。换言之,烟草行业用“专卖”的外衣将其产业链条中的利益全部捆绑拟制为一个“专卖利益”,使得所有违反烟草专卖的经营行为都轻易满足非法经营罪中关于“违反国家规定”的入罪门槛。正因如此,在对涉烟类非法经营罪进行认定时更加需要对其他要件的符合性,尤其是实质要件的符合性做谨慎的判断,更需要在“适用刑事处罚”与“适用行政处罚”之间谨慎判断,以避免扩大刑法处罚范围,避免因实践中要件判断的缺失而将行政立法实质上等同于刑法立法,剽窃了刑事立法的绝对保留权。
涉烟类非法经营罪的实质要件的判断,也要围绕“市场秩序”这个法益。烟草专卖作为行政许可,在行业准入的层面上,本身就属于市场秩序的一个部分,但并不是全部。不能仅因行为破坏了专卖制度而直接认定为破坏了市场秩序,否则定罪的涵摄将在“违反国家规定”和“扰乱市场秩序”两个要件中自我演绎、自我论证,放大行政许可在市场秩序中的权重。
“扰乱市场秩序”是规范的构成要件要素,在烟草专卖的语境下讨论非法经营罪的认定,应当结合烟草专卖的立法旨意和非法经营罪的保护法益共同考量。其内容大致可以分为五个方面:违反行政许可的严重程度、对消费者利益的损害程度、对烟草行业利益的损害程度、对国家财政利益的损害程度、对国家资源配置的损害程度。
三、以案例导入讨论涉烟类非法经营罪的犯罪形态
【案例】(2021)
2019年,贵州籍被告人徐某在向贵州当地烟农非法收购烟草站不收购的烟叶后:1.销售给刘某23600斤(11.8万元),刘某将烟叶进行二次转卖。2.销售给湖北籍烟农全某等人6000斤(3.3万元),全某等人将该烟叶转售至湖北当地烟草站,用以冲抵因灾情无法完成的烟草种植任务,缓解经济压力。3.第二次销售给全某9000斤(4.8万元),但在运输途中被查获。4.查扣徐某尚未售出的烟叶共计63540斤(评估价值31.77万元)。
案件办理过程中,检察院将徐某所销售烟叶、被查扣烟叶均认定为非法经营罪既遂(51.67万元),认为其违反国家烟草专卖管理法律法规,未经烟草专卖行政主管部门许可,非法收购烟叶并销售,扰乱市场秩序,情节特别严重。
(一)从实质要件符合性的角度讨论
徐某收购烟叶并销售的行为已明显违反烟草专卖相关规定,但需要对其涉案金额进行实质性的认定。
在第1笔交易中,徐某销售的烟叶被二次转售,具有被下游买家制作伪劣香烟销售、侵害消费者利益的风险,由此分流的制售行为,也可能对烟草行业利益、国家财政收入、国家资源配置造成一定程度的损害。但造成这种风险是否就应当认定为非法经营罪既遂仍需讨论。
在第2笔交易中,徐某销售的烟叶被全某用于冲抵当地种植烤烟的任务,最终由烟草收购站收购,并未流入外部市场。因烟草站收购烟叶有质量及数量标准,其收购的烟叶最终不会影响烟草制品质量及价格,故不会对消费者利益产生损害。同时,因为烟草站收购的烟叶仅在烟草行业系统内部流转,不会对烟草行业、国家财政、国家资源配置产生负面影响。相反的,在湖北当地烟农因自然灾害而不能完成种植任务的时候,徐某的销售行为一定程度上帮助了当地烟农增加种植收益,帮助当地烟草公司增加收购总量,变相地帮助增加了烟草制品产量,增加了行业效益、国家财政收益,故该笔交易不符合侵害市场秩序的实质要件,涉及烟叶数量及金额不应当纳入非法经营罪中进行认定。
在第3笔交易中,徐某的出售对象同第2笔交易一样均是全某,且该笔交易尚未完成,就法益侵犯的角度来看,明显更低于第2笔交易的情形,故第3笔交易同样不符合实质要件,不应当认定为非法经营罪。
在第4笔交易中,查扣的烟叶数量较多,但均处于尚未销售、甚至尚未意定买家的状态。由此该行为对市场秩序的侵害程度,除开违反行政许可的情形以外,其余各利益仅处于被侵害的危险状态。对于此种状态是否应当认定为犯罪行为的既遂,需要更为深入的讨论。
(二)关于是否具有未遂情形的讨论
非法经营罪没有未遂不仅是涉烟犯罪司法实务的主流做法,亦为刑法理论界所广泛认同。如有人指出,“非法经营罪是一种行为犯,并不以特定结果发生为既遂要件。”“由于非法经营罪为行为犯,一旦行为人实行了非法经营行为,即为既遂。”有人则进一步指出,“在非法经营犯罪活动中,非法经营表现为生产、运输、储存、销售等多种行为方式,只要行为人实施其中的一种行为,就侵害了国家限制买卖物品和经营许可证的市场管理秩序,对于情节严重的,构成非法经营罪,而且为既遂。行为人是否完成销售行为,只是造成危害社会后果的程度不同而已,并不影响非法经营罪既遂的成立。”
最高人民法院第97号指导案例将“违反国家规定”与“严重扰乱市场秩序”明确独立为两个要件,使该罪的两个要件从文意上便构成了结果犯,即既要有违反国家规定的行为,又要有严重扰乱市场秩序的结果。由于“市场秩序”是一个经济学概念,一个行为引发市场秩序的变化状态呈现周期长、结果多样、原因多样等复杂情形,所以对该行为结果进行实质性要件符合性的审查时,必然将出现该罪是“处罚实害结果”还是“处罚危险状态”的判断。
若以处罚实害结果为标准,即认为该罪属侵害犯,则当实害结果尚未发生时,应当认可该罪存在未遂形态。以本节引述案例来看,徐某第1、4笔交易均仅主要造成了法益受到侵害的风险,并未发生实害结果,故应当认定为未遂。
若以处罚危险状态为标准,即认为该罪属危险犯,则行为发生了行为人追求的、行为性质决定的危险状态时,成立既遂。以本节引述案例来看,徐某第1、4笔交易均造成了法益受到侵害的危害风险,故应当认定为既遂。但此种既遂的状态是否值得刑法的处罚?
由于现实生活中出现了高度危险来源,危险行为一旦发展成为侵害行为,其对人的生命、身体、财产造成的损失就不可估量,因而必须在形成侵害前,对危险行为本身进行刑法规制,从而周延地保护合法权益。所以危险犯已经将犯罪的处罚时间及范围进行了立法上的扩张,其本质是未遂犯的正犯化。
刑法具有谦抑性。只有在运用民事的、行政的法律手段和措施仍不足以抑制时,才能运用刑法的方法。就徐某的第4笔交易而言,其行为对于法益的侵犯仅处于一种抽象的危险状态,将仅有收购行为的违法行为认定为非法经营罪的既遂形态予以处罚,明显在危险犯的基础上再次扩张了非法经营罪的处罚范围,失去了刑法适用应有的谨慎,将违反行政许可规定与否作为刑法适用的唯一度量,这是明显不适当的。
结语
涉烟类非法经营罪因其专卖的行政垄断背景,使其成为众多非法经营行为中较为特殊的一种。其垄断的性质,使得该行业对于扰乱市场秩序的容忍度极低,为保障行业、人民、国家的相关利益,不断延展处罚范围。最终导致涉烟类非法经营罪在认定的过程中,行政权力所扮演的角色逐渐占据主导地位。
与此相对应的是,司法人员过于依赖司法解释对于入罪金额的形式要件的认定,而忽略了该罪所保护法益的考量,致使在涉烟类非法经营行为是否入罪的判断中,行政维度的认定拥有了主要的话语权。
更为遗憾是,在实践中对于非法经营罪未遂形态的否定成为裁判惯例,在形式上确实通过违法行为的处罚而保障了人民、市场、国家的相关利益。但是其违背刑法原理的行为逻辑,破坏了刑法应有的稳定和谦抑,长远看来,对于上述利益的破坏反而是更大的。
由此,笔者认为,当涉烟类经营行为出现违法时,应当从刑法的本位出发,更加深入地分析构成要件的符合性,在充分考虑应用行政处分手段评价其违法行为后,再慎重适用刑法,以保障人民根本权益,为实现全面依法治国目标贡献司法力量。
参考文献:
1. 《中国烟草概况》,中国烟草官方主页,2021年。
2. 《不要让烟草夺去你的呼吸》,世界卫生组织官方网站,2019年5月29日。
3. 《中华人民共和国烟草专卖法》第五条规定,国家加强对烟草专卖品的科学研究和技术开发,提高烟草制品的质量,降低焦油和其他有害成份的含量。
4. 张明楷:《刑法的私塾》,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7月第1版第3页。
5. 崔志伟:《非法经营罪中“严重扰乱市场秩序”的教义学解读——以最高人民法院第97号指导案例为基本视角》,《中国检察官》,2020年第1期。
6. 陈兴良:《非法经营罪范围的扩张及其限制——以行政许可为视角的考察》,《法学家》,2021年第2期。
7. 张建、俞小海:《涉烟非法经营罪未遂之辨正》,《法学》2013年第2期。
8. 李斌:《翻印非法出版物构成非法经营罪》,《人民司法》1998年第7期。
9. 顾万炎:《对“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的重新理解》,《中国检察官》2O11年第2期。
10. 贺平凡、罗开卷:《涉烟犯罪的罪数形态认定——析<关于办理非法生产、销售烟草专卖品等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政治与法律》2O11年第7期。
11. 张明楷:《危险犯初探》,《清华法律评论》,1998年第1期。
12. 陈兴良:《刑法哲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7页。
宁波刑事律师,你身边的律师帮手,13605747856【微信同号】
继续阅读

我的微信
如果以上文章对你有帮助
扫一扫,加律师的微信,了解更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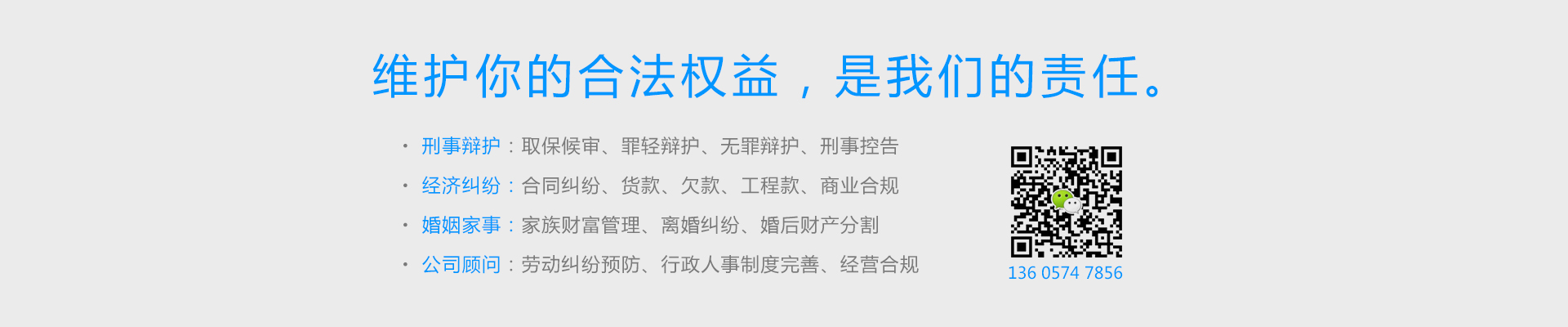

评论